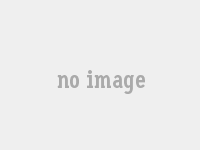一个、两个、三个……十个,白书领、白海民、白会光……张爱清,一个数字对应一个名字。
每增加一个数字,就直接意味着河北邯郸成安县白范疃村在江西丰城发电厂坍塌事故中遇难的村民又多了一个。
11月24日,钢筋和水泥块伴随着巨响轰然倾倒而下,76名施工工人瞬间被掩埋。74名遇难者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在顷刻间都失去了依靠,其中距离江西丰城千里之外的河北白范疃村就有10名村民遇难。
一个月后,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全国爆料热线:M17702387875@163.com)在白范疃村采访时发现,10名遇难者事成了村里不能触碰的伤痛,尤其对于家属来说,甚至不愿相信这是已发生的事实,“不说没事,一说就哭。”

白海民和妻子的合照。
村庄的哀伤,遇难者大多集中在同一区域
早上9时许,和煦的阳光开始把路上凝固的冰渍融化,却没有把冷了一夜的白范疃村唤醒。村里巷道分明,差不多3米的高墙和紧闭的大门将每家每户都裹得严严实实。在这个冬季,路上很难看到人影。
头七、二七、三七、四七……在北方传统的农村里,对于祭奠每一个逝者的七天都很重要,与以往不同的是,白范疃村的家属们给10名遇难者上坟,哭声总能传遍村庄前后——他们的坟地埋在不同的方位。
白范疃在北方是个相对一般的村子,全村人口约2400人。人均耕地面积不多,平时不少村民常靠打工补贴家用。
在村民的眼里,他们和10名遇难者的关系不仅仅是乡里乡亲,甚至有些还是非常近的本族系。除了这些遇难者的逝去对他们来说比较震惊外,他们几乎知之不详,“都基本常年在外打工,事情只有他们家里比较清楚。”
差不多10点钟,上游新闻记者向几名村民一一打探白书领、白海民等10名遇难者的住所,无一不能获得准确的指示。
村民白玉书和他的儿子在事故中双双遇难,他们也是村里唯一一家同时逝去两个人的家庭。
记者进入白玉书家时,这个家庭正在吃早饭。听到陌生人进入,房间的帘子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他自称是白玉书的兄弟,“谢谢你们的到来,我们不想说了,太惨了。不想说了。”
和普通人家不同的是,遇难者白松松、白俊海、白书领等人的家大门紧闭,即便敲门过后,也无任何动静。
白海鹏家在白范疃村的西南角,同样大门紧闭。
邻居说,白海鹏是家中独子,多年前就和妻子一起在外打工,很少回家。家里现在有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有精神疾病的母亲。
白范疃村此次逝去的10名壮劳力,几乎全部居住在村子西南区域,甚至同一条巷子里就居住着两三户。
“梦里看不清他,我一喊他,他一回头,就没了”

白海民秋天回来时给家里安置了新的暖炉。
34岁的遇难者白海民家和另一名遇难者白俊海家在巷子里大门对大门。白海民去世后,家里就剩他的妻子和2个孩子。
他的妻子个子不高,语气温和有礼。她把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棉被折叠成豆腐块状和枕头摆放好。每天接送完孩子后,她通常收拾收拾屋子,“这一天也没什么了”。
房间的陈设很简单,铺着床单的床占了一大半。床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他们夫妻的婚纱照。
他们是经过介绍认识并结婚生子的。尽管他们的婚姻没有充满对爱情的想象,但感情却很好,“结婚十来年了,从来没吵过架,连拌嘴都没有”。结婚不久后,白海民就跟着村里人到外地打工挣钱养家。
白海民平时外出打工一年才回来几次,不过他们两口子基本上保持着每天两次通话,早晚各一次。妻子常叮嘱在工地的白海民要注意安全,“要记得戴好那个帽子(安全帽)”。
白海民之前到过宁夏银川,后来又转到江苏淮安,最后到了江西丰城,主要工作是搬钢筋,“做的都是最重的体力活”。
秋天,在完成淮安的工程后,白海民曾经回到白范疃村呆了几天。看着天气渐冷,他专门购置了新的暖气炉。就在事故发生的前两天,白海民还在电话里问李素素“暖炉有没有点着,好不好用”。
事故发生的前一个晚上,白海民如往常一样和李素素通电话,对话还是依旧的平淡。
第二天孩子上学后,她接到别人的电话说,江西工地上出事了。她心里还在纳闷,就说了句:“怎么可能呢,昨天晚上还通过电话,都好好的。”
白海民的妻子始终不放心,就走到了巷子口的白松松家里,这个家中已是乱成一片,家人们拿着电话,表情十分紧张。
“有你家的,你家海民也在……”对方话未完,白海民的妻子昏厥了过去。
从江西处理丈夫的后事回来,她说很少睡觉,即便睡着了也常醒来。
“这几天不断的重复同一个梦,他掀开家里的帘子,看也看不清,我一喊他,就没了。”白海民的妻子说,每次惊醒后,李素素就再也难以入睡,一直想着,一直哭。
她的手不停地擦拭掉落的眼泪,“都是假的,啥也是假的。我都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太阳,我就愿意在这黑暗的地方一直坐着,一直坐着。”
她觉得,黑暗给她一种天还没有亮自己还在做梦的感觉,一切都是噩梦。
可这个梦的名字叫做现实,这是一场永远都不能醒过来的噩梦。
她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她要为现在才6岁的小儿子筹备未来的事宜,尤其是结婚用的钱——买车、买房、彩礼,加起来要几十万。
“她在坟地里哭了三个小时,拉都拉不起来”

白会光的父母已经70岁了,儿子去世后留下留下两个小孩需要照顾。
白范疃村在江西丰城发电厂坍塌事故中遇难的10人,其中有7人来自同一个家族,另外一个姓张,还有两个白姓的属于另外一个家族——白伟光和白会光,是亲叔伯兄弟。
白会光的母亲态度和善,说话时语速平缓,她今年已经69岁。
白会光在外打工差不多已有10年,是从婚后开始出门打工的。
江西丰城事故发生前,天气渐冷,他回了一趟家,带走了过冬的厚衣物。
白会光的母亲并没有到江西去,她从回来的人口中听到关于这场事故的很多消息,包括事故原因,“有些人为了得利,才弄成这样,这对多少家庭造成了多大伤害呀!”
白会光今年才31岁,膝下有一对儿女,姐姐7岁,弟弟5岁。白会光的母亲感到十分无力,她没有抽泣就流下了眼泪, “我现在69了,家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白会光的父亲把两个放学的孩子接回家来,姐姐一进门就大声喊着“奶奶”,小弟弟就缠着爷爷玩。白会光的母亲看着小弟弟,说:“家里就这两个孩子,走一步看一步,孩子最可怜。”
每个祭奠日子,百会光的父母和妻子都会到不远的坟地里给他烧纸,诉说自己的思念之苦。
三七那天,一家人9点过就到了坟地,青青的麦苗地里,上面覆盖着花圈的一座新坟异常醒目。
白会光的母亲烧完纸后,哭诉着遇难的孩子,她觉得内心深处的压抑要靠哭诉才能够完整的表达。
“她在坟地里哭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拉都拉不起来,我说咱得回家给小孩做饭了,还是不停的哭,到后来我们把她架了回来。”白会光的父亲说,孩子去世了,每个人心里都难受。
“家里八口人,压力大,支出基本靠打工”

白臭臭在亿能公司上班时佩戴的工作证。
事故中,白范疃村虽有10人遇难,也有两名村民平安地回来了。一个是白敬伟(音),一个是白臭臭。
白敬伟回到村里之后不久又马不停蹄到天津打工去了,留下了妻子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家。虽然听白敬伟提到过江西丰城的事故,但他不具体说,妻子也识趣地不问。
他们夫妻俩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例如这次白敬伟离家打工,具体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白敬伟的妻子基本是“不知道”。
和白敬伟的“闯劲”不同,自认“胆小”的白臭臭在事故回家后就没有再离开村子,冬季本就是农闲,白臭臭常在村里来回转悠着聊天度日。记者找到他家时,白臭臭从早上已经出门了,“估计吃饭的时候就会回来”。
丈夫平安无事归来,白臭臭妻子的脸上时常挂着乐天的笑容,当上游新闻记者向她确认“白臭臭”的名字时,她乐呵呵地笑道:“自大加一点,原来叫白腾飞,登记名字的时候写错了。”
妻子的菜刚炒好,白臭臭回来了。这个大概一米六多一点的男人在北方已属个头矮小,他穿着土黄色的外套,给人以敦实感。
白臭臭到江西丰城工地做零工大约只有1个月,他有着粗线条的思维——除了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按时上下班,其他事情他不去多管,也没有多想。
他知道从生活区到工地骑自行车大概要十几分钟,自己一天工作大概六七个小时。至于施工单位有没有给自己买保险、工资什么时候结算一次、当时施工单位有没有赶工期等等,他说自己都不清楚。
卧室靠近门口的挂历上,还挂着他的工作牌:江西丰城电厂三七扩建工程,白臭臭,木工,河北亿能。
虽然工作牌上写的是木工,实际上“哪里需要人就去哪里”。他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头上的建筑结不结实,脚下的混凝土稳不稳固。
事故发生的前,他一下班后就倒头休息了,直到几个小时候听工友说起工地上出事了,他才直到真的出事了。
白臭臭没有到工地去,“我胆小”,就算场地陆续清扫完了之后都不敢去看。但他也没有离开,就停留在生活区等着结算工资。事故后发生后的七八天,白臭臭带着领到的万元左右的薪水回到了白范疃村。
白臭臭说,以前在家里做做零工,但收入很不稳定。这次到江西打工就是冲着“挣钱稳当”去的。事故之后,家里人都知道白臭臭口中所说的“挣钱稳当”其实并不稳当,回来之后就不准他再去了。
白臭臭说年前哪里都不去了,在家里呆着陪陪家里人,过完年之后还是要出去打工,“家里有3个孩子,还有父母,奶奶,一共八口人。父亲身体也不好,压力大,额外支出基本都靠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