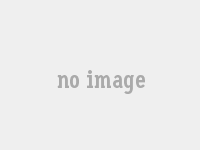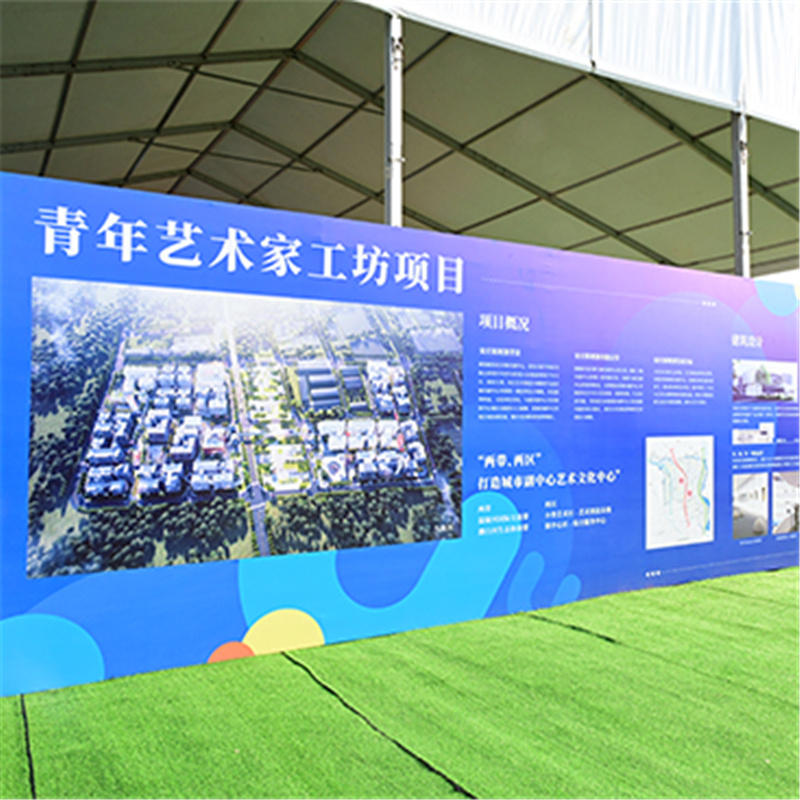去年秋初至年底,几位传统艺术的代表人物相继离世。尤其是单田芳的与世长别,激起了人们对评书艺术的怀念,也引起关于单田芳之后评书艺术如何传承的担忧。
单田芳的评书有他鲜明的个性特征,沙哑但却富有表现力的嗓音,表演时饱满的情绪所传递出的强感染力,以及对古老评书融入个人风格的创作,使得他的演播作品有单刀直入的快节奏,聆听过程扣人心弦。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这个说法一方面说明单田芳的评书很接地气,另一方面也客观表达出评书传播渠道的单一与庞大。在收音机未普及之前,评书是街头艺术,演员需要在公共场合与观众面对面,而在几乎家家一台收音机的背景下,评书演员第一次借助现代媒介,成为过去时代的明星。
收音机的便携性打破了评书传播曾经口耳相传的特征,解放了听众的收听限制,在田间地头、庭院餐桌,大人与孩子扭开旋钮,即可在固定时间听到讲得栩栩如生的评书故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造星机制,而单田芳则是收音机时代造就的明星。
当然,听评书之所以在过去成为最主流的娱乐享受之一,在于它富有丰富的文学汁液,它的文学性来自于《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杨家府演义》《英烈传》等古典著作,也来自于评书艺人以口头文学表达形式为这些古典著作灌注的民间情感,两者融合,才缔造了评书强大的传播力与生命力。
“单田芳在民间的影响力一度超过金庸”,有媒体在单田芳去世后如此表示。这个观点并不夸张。金庸小说盛行时,虽然阅读门槛也不高,但在底层表达上,单田芳的无死角传播,还是更胜金庸一筹。对于为何不把金庸小说以评书形式表达出来,单田芳的解释是,金庸小说太过严密,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这个解释被网友解读为单田芳的“情商高”,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评书与金庸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两者没法很好地相融。
如果说金庸小说在纯文学时代以其通俗性博得了大众读者的喜爱,衔接了古代侠义小说与现代文学的疆土,凸显出重要的文学地位,那么,单田芳等评书艺术家演播的评书作品则衔接了通俗演义小说与民间口头文学之间的空白位置,填补了广大民众想要亲近文学的娱乐需求,同时,评书也从最基本的层面启蒙了无数人的童年,对正邪、善恶等正向价值观有了初步的认识与判断。评书的伟大,是被低估了的。
在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公众主流娱乐载体之后,评书市场便开始萎缩了。常宝华与其弟子侯耀华、牛群等通过央视春晚等电视平台,成为举国知名的演员。相声的辉煌源自于它的常说常新,在创作上,当年的相声能够联系实际,把社会时事融进作品里,有针砭时弊的功效,所以相声艺术的顶峰是在电视时代被创造出来的。同一时期,评书作品虽然也有创新尝试,但由于篇幅长,改编难度大,在与相声的竞争中落了下风。一直到今天,评书爱好者们最喜爱听的,仍然是早期的经典评书。
由此可见,仅就相声与评书这两种传统艺术形式而言,传播载体与内容创新决定了它们的活力。侯宝林、马三立、马季、侯耀文、唐杰忠、李文华等每一位相声艺术家的去世,都会引起一阵对相声沉寂的叹息,所以常宝华、师胜杰、常贵田去世时,人们对相声的感慨与以前也是大致相同的。电视的盛行,降低了评书的热度,而相声的陨落,则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难发现,娱乐越是多元化,传统艺术的竞争力就越弱,这是大势所趋,几乎难以阻止。
但经典作品的魅力,是可以穿透时光的。在今天,仍有数量不少的年轻人在通过汽车收音机、互联网电台、智能手机APP等渠道继续听相声、听评书,也就是说,哪怕这两门艺术不做任何形式的传承创新,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有人循迹而来,成为它们的热爱者,这也决定了,只要肯用心,在肯定传统艺术的独特价值基础上,进行一些大胆的改造,必然会延长传统艺术的生命力。
为了宣传《江湖儿女》,导演贾樟柯录制了抖音小视频,接受了B站采访,对修音、鬼畜等新表达形式进行了亲密接触,这是明显地在向90后、00后们靠拢,吸引他们来观赏一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导演的作品。像贾樟柯这样的姿势倾斜,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态度——他不愿自己的电影再是小众文艺片,而是渴望被更多年轻人接受与了解。这个事例,其实值得相声与评书的传承人去研究与学习。如何通过拓展渠道来扩大受众群,又怎样把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融入内容,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但值得去征服。
传统艺术的继任者们为了把“祖业”传递下去,就先要抛弃观念上的负重,不以过去的辉煌为压力,不以当下的寂寥为包袱,更不要恐惧适应与变化。对经典的改造与颠覆,注定要承受一些指责,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花样翻新,也一样会引来别样的目光,但只要有底蕴打底,有热爱当先,传统艺术就有很大可能在新媒介平台与陌生受众群那里开出崭新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