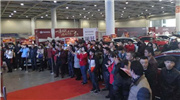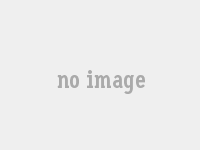小的时候,屁事儿不懂,跟小伙伴们笑闹时会说到一句不是老天津卫人不懂的话:
“你是打吴家窑跑出来的吧?”
加标点符号共十四个字符,说起来抑扬顿挫,大家哈哈一笑,继续你追我赶,没心没肺。
诸君且看,吴家窑是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来解惑。
很多很多年前,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吴家窑建起来,偌大的天津市,仅此一家,所有精神不正常的患者均被送至此处,于是连同整个吴家窑区域都成为了大家口中的“精神病院”。
“你是打吴家窑跑出来的”——并不是一句骂人的话,大抵用于熟人之间的玩笑。然而虽不骂人,却很伤人。
这个道理在我二十年后前往河西区精神卫生中心(天津圣安医院)纪实拍摄,才真切地感受到。

昨日,尚未亮明身份,在大厅坐等同事之时,听见两名家属的对话。
“你儿子是为什么得病的啊?”
“唉,别提了,他刚成年那会儿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被骗了,不只是骗钱,我们儿子去讨要公道,那人还追着我们儿子打,我们儿子跑回家来,那人也不放过,带人追到家里打。你说人家有本事的都能给儿子拔怆(报仇),我没用啊,没本事,只能劝儿子忍,这一忍,忍出病来了,我后悔啊,早知道这样,我不要命了也给他讨个说法。”
“那你们当家的干嘛去了?”
“早死了。”
我忍不住想象当时的场景:单身妈妈眼看儿子被围着打,却并没有冲过去抱住他,此后儿子沉浸于永久的痛苦当中,妈妈也因汹涌的愧疚而饱受折磨。
或许,“忍”之一字才是真正致病的根源,它犹如一股气,堵在胸口,一点一点往里揪,直到那个少年整个人被揪得像打了乱结的绳子,舒展不开,有力无处发,妈妈不得已,又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只好将他送入医院。
“我没什么钱,但捡捡瓶子还能凑齐住院费,送他进来治病是我最后能做的了。”
“送医院好,送医院好。”
“嗯,听说我儿子今天都会唱歌了,我得去看看。”
她说这一句时,站起来抬腿就走,脸上露出难得的喜悦,她身后拖着一个简陋的大行李箱,里面应该放着给儿子携带的吃穿用品吧。我很想跟在这位母亲后面一起去看看,可惜我还要等人,我想,不急,一会儿正式开联欢会,总能再遇到。
下午一点半,院领导们和“佳人”们一起,开始了一场辞旧迎新的联欢会。
此处“佳人”是天津圣安医院为患者们重新定义的称呼,一是谐音“家人”,二是盼望他们早日康复、身体佳健的美好祝愿。
联欢会嘛,很欢乐的气氛。一长发飘飘的男子领头唱院歌,字正腔圆,婉转动听。

大哥,你真的是患者吗?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定位?你要是不穿着病号服,我还以为你是一艺术家。
我隔着镜头给他拍了好几张特写,他唱完歌笑眯眯地唤我“摄影师”,请我帮他给病友与护士长合照。

后来我听见他说他喜欢有月有雾的逍遥日子,有一回犯过病清醒的片刻,家里人让他来住院,他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自己住进来了。
真 · 艺术家。
他唱罢,大家都来了兴致,一边齐声歌唱一边表演手语操。
我在镜头里记录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忽然想:你有酒,他们也有酒,你有故事,他们也有故事。干嘛以正常人自居,而把他们视为异类?
信息不对称会带来地域黑,双眸不平视则带来分别心。
镜头所及之处,是这一方小天地的人生百态,一位老爷爷一直在抹泪,哆哆嗦嗦,望着相隔一条过道、队伍里正唱歌欢笑的他的亲人,边哭边说:“要是没病多好…要是没病多好……”
他孤身一人,约莫80来岁,茕茕孑立。不知道他想起了怎样的过往,只是瞧着他摘掉眼镜不停抹泪、泪珠游曳过皱纹的样子,仿佛一颗心被生生剜走。

爷爷旁边的病友家属说:“还好这医院的医生护士好啊,把他们当自己孩子一样照顾!”
“是……是……”爷爷又哭了。
另一个镜头里,一位上了年纪的婆婆缓缓地剥开一只香蕉,举在对面的亲人面前,那么耐心地等着,等着对方接过去吃下第一口,等待期间婆婆偶尔问上一个问题,但对方不回答,只默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举着相机,闭着一只眼睛等得眼皮不自觉抽搐,才捕捉到这一交接。当男人开始安安静静地吃下第一口香蕉,婆婆也终于欣慰地托着下巴观瞧。

后来我听到那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男人小声说:“我每天都想你。”
还有一个镜头里,也是一位婆婆,她不肯让眼泪掉下来,拿手擦了两把以后索性蒙着纸巾哭。

我问:“是心里难受么?”
她说:“是高兴啊!他能和大家在一起唱歌,一点儿都……一点儿都不像是病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我也哭了。
应向哪方哭你?教万林婆娑,教金乌跌落。
须臾间天地落魄,求造化从轻发落。

其实,对于这些“佳人”们来说,自暴自弃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挽救他们的办法却也很简单——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给予他们真心的温情陪伴和专业的治疗照顾。
芸芸蜉蝣世,愿你们在圣安,如溺者逢舟。